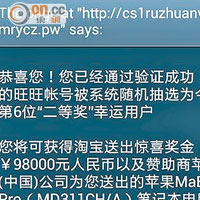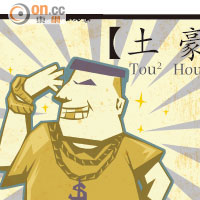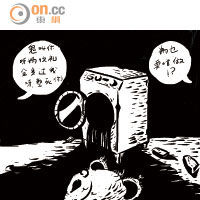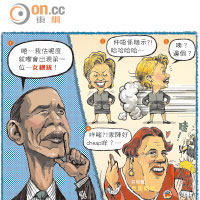一九四三年的開羅會議,中國已抗日六年,羅斯福對華亦向有好感,頗有意把中華民國扶持為戰後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夥伴,故此《開羅宣言》的條款對華十分有利,與廿四年前(一九一九年)中國在巴黎和會的處境判若雲泥。
但會後不久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:「……發表開羅會議公報以後,中外輿情莫不稱頌為中國外交史上空前之勝利,寸衷惟有憂懼而已。」為何如此呢?
開羅會議召開時,仍為大戰中期,歐亞有不少地方仍待盟軍解放,制訂擊敗軸心國的戰略,才是會議首要議題。站在中方觀點,從日本手上奪回緬甸,重新打通滇緬公路的生命線,乃燃眉之急,蔣介石希望「遠征軍」在緬北發動攻勢,英美在緬甸南岸登陸策應,兩面夾擊,一舉成事。
但在美英的戰略是「先歐後亞」,籌劃中的一九四四年初夏諾曼第大登陸,才是他們眼中的頭等大事,故此他們對蔣的建議冷淡對待,其後國軍更被迫在緬北獨力反攻。以往不少傳統華人史家對此大感不滿,然而國際政治是現實的,大國以己方利益為先,才不會「毫不利己,專門利人」。
會議結束後,蔣介石回國,途中到了「遠征軍」的駐紮地視察,他眼見受美式訓練的國軍官兵質素,與西方軍人仍有差距,慨嘆中國尚需廿年努力,才可追上列強,關鍵在教育,如不努力,將永不得西方平等看待。七十年過去了,明天以此間中國的國際處境總結。
(《開羅宣言》七十周年紀念之五)
黃毓民 立法會議員